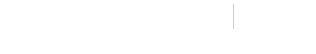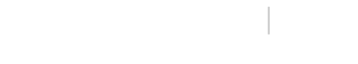故事主人公:杨守森,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5年出生,山东高密县人,祖辈皆农民。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老家,担任过团支书,当过公社电影放映员。1977年参加高考,考入山东师范学院(山东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谈起40年前的高考,杨守森感叹道:“它确确实实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我这样一个农民之子来说,这到手的一纸录取通知书,意味着可以吃国库粮了,可以由乡下人变为城里人了,算是一步登天了……”
差一点留在老家当“村官”1974年,高中毕业,杨守森便回到农村老家,当起了农民。于农民出身的杨守森而言,农村生活并没有太多不适,高密县那个小村庄,是眷顾这个年轻后生的。“那里虽贫穷落后,但有一些很喜欢读书的年轻人,《苦菜花》、《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艳阳天》,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一些 红色经典 ,常在他们中间传阅、讲述。受大人们影响,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也半通不通地跟着他们读过一些。大概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不知不觉地对文学产生了兴趣。”回村劳动了几个月之后,厚爱他的班主任綦老师,把杨守森推荐到了公社三秋会战指挥部,帮忙统计生产进度,下村送送通知。在这期间,他得到了公社干部老陈的赏识,希望他回到村里担任团支部书记。
当上团支书之后,他积极地开展一些团的工作,现在回想起来,最让他激动的是,他曾组织村里的年轻人,排演过据刘知侠的小说《红嫂》改编的革命现代京剧《红云岗》。演出那天,居然招来了周围村子许许多多的观众,令他们那个小村很是自豪了一阵子。
因为当过团支书,杨守森与小村庄就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使他更多了一些关于年轻时代的甜蜜回忆。在杨守森的博客里,时常描述他那个小村庄,那里的一湾一水,一老一少,都成为身在都市的他夜深人静时的写作素材。
杨守森给记者看了1974年,他所在的袁家人民公社高中四级一班全体同学毕业合影,计54人,一个个都是聪慧纯朴的乡间少男少女。“我上高中期间,大概与邓小平复出有关,有一段狠抓教育质量,老师们极尽其职,同学们勤奋刻苦,如在当今,估计至少会有过半考取大学。惜乎生不逢时,我的大多数同学的才华被埋没了。”说起往昔,不胜唏嘘。杨守森与他们不同的一点,或许就是,毕业之后,不论在田间地头,还是从事其他工作时,都从未放弃过文学梦吧。一边放电影一边备考。
后来,缘于一个极为特殊的机遇,杨守森被选中,留在公社放映队当了电影放映员。放映员不只是放电影,还要自编自演节目,负责文艺宣传等,这对本来就喜欢看书、写东西的杨守森来说,倒正是天随人愿,也为他后来能够参加高考提供了可能。
杨守森是在公社放映队参加高考的,是他中学时代的毛老师托人转告了他恢复高考这一消息的。“由于孤陋寡闻,在填写报名表时,我竟闹不清大学里还有文理科之别,一切都是遵循了毛老师的建议。报的文科,第一志愿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泰安师专中文系;第三志愿记不清了,第四志愿是服从分配。”
11月20—25日报名, 12月9日考试,杨守森清晰记得当时的时间。文科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历史、地理、政治、数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像样地复习四五门课程,显然已是不可能。“语文与史地,由于内容漫无边际,干脆放弃了,政治一科,只是反复背诵了叔叔从外地给我寄来的实验中学编写的一份复习提纲。其余的时间与精力,就全部放到数学方面了。”他回到在农村家中,将初、高中学过的数学课本全部翻找出来,抖去上面的尘土,打进了走村串乡时的铺盖卷里。“我的放映队长及队友给予了我全力支持,不仅安排我休了几天班,还让我在那段时间里只负责看管发电机。这样,每天晚上,放映开始,当人们全神贯注于银幕上的枪声炮火时,我就可以躲在远处明亮的电灯光下,伴随着发电机的隆隆轰鸣,进入另一个数学王国。”
考试结束后,杨守森的第一判断却是“完了”。虽然凭依原来的兴趣与积累,语文知识与那篇《难忘的一天》的命题作文,自觉尚可;仰赖了实验中学的那份复习提纲,政治可能也不会太糟糕;但中学时代没怎么学过的历史与地理,心里就没底了。
后来,杨守森才知道,当年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自己无疑是幸运的,当时我们全公社考上本科的,只有两个人,我与另一位高我一级的同学。” “没参加高考,可能是个不入流的作家或农民” 在中国的大学招生史上,1977级的学生成份大概是最为复杂的。除了极个别年龄较小的应届生之外,大都有过几年不同的江湖阅历。杨守森的同班同学中,就有下乡知青、退伍军人、码头搬运工、手艺高超的木工、武术教练之流人物。至今,老同学们聚会时,他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还是:当年江湖上的风风雨雨。
尽管作为师范院校,培养目标是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但杨守森从内心里不想这一辈子仅仅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学语文教师,他还梦想兼顾着成为一名诗人什么的。于是,上课之余,他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读诗、写诗方面。“我一直订有1976年复刊的《诗刊》,每逢刊物到手,我都会发狂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诗经》、《离骚》、《唐诗三百首》,都是下过一番背功的;学校图书馆里,凡当时已经开放、得允借阅的古今中外诗集,差不多都借阅了一遍;甚至曾有过一天写十几首诗的狂热。”这些努力,对于杨守森后来所从事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颇有益处。
而实际上,在当时的同班同学中,不甘心于仅仅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者,大有人在。“或像我一样醉心于诗歌,或主攻小说,或操练散文,或梦想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这些同学,都不怎么看重考试成绩。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在周六下午,商量各种理由,请假外出,结伙野游。“那时,学校没有南门,但有一道可以爬越的矮墙,校园南面不远处就是庄稼地,就是千佛山。那时的千佛山,也还没有圈起来卖钱,可以随便出入。于是,我们可以穿过田野,登上千佛山,直奔大佛头。然后,在乱山中瞎转一气,海阔天空,激扬文字,一直到傍晚,才赶回学校。”转眼,就要毕业,杨守森的意愿是回到原籍,且已联系好县文化馆,希望能有条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以实现成为诗人的梦想。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领导找他谈话,要他服从分配,留在本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我不清楚领导依据了什么,后来听说,是因我曾在《山东文学》发表过几首小诗,一篇小说评论,是时任《山东文学》评论组组长的陈宝云先生,向他的老同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李衍柱老师推荐的。我猜想,还应该与本系教授、著名诗歌评论家冯中一老师有关,因为喜欢诗歌,冯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关爱与扶持;我的那篇关于郭小川诗歌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经由冯老师亲手指导,推荐给学报发表的。”杨守森有点愧疚的是,“那时,因痴迷于写诗,弄得学业实际不怎么扎实,各科成绩也都平平,实在算不上好学生。”杨守森回想自己的人生历程,虽也多经磨难与挫折,但幸运的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每一个关键时期,或危难之际,他都遇到上了好的师长。这让他一个农村娃娃得以走出高密县的小村庄,成为深受学生爱戴的“杨老师”,并将师德代代传承。 “如果没有参加高考,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不入流的作家吧,又或者是农民。”杨守森说。正如杨守森所感叹的:“人生际遇有时实在是很难参透的事情”。
编辑:单博平